江勇振著胡适传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使得我们原本认为简单清晰的胡适的形象变得模糊起来。它告诉我们:我们离真实的胡适还远着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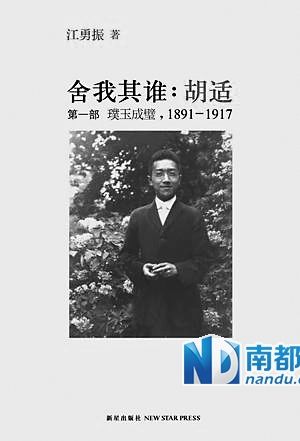 《舍我其谁:胡适——— 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江勇振著,新星出版社2011年4月版,88 .00元。
《舍我其谁:胡适——— 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江勇振著,新星出版社2011年4月版,88 .00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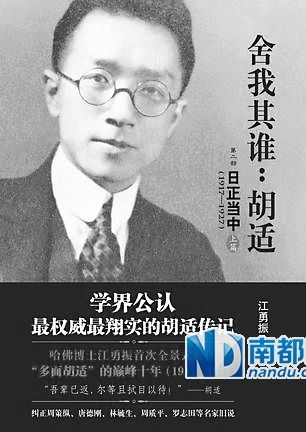 《舍我其谁:胡适——— 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江勇振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98.00元。
《舍我其谁:胡适——— 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江勇振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98.00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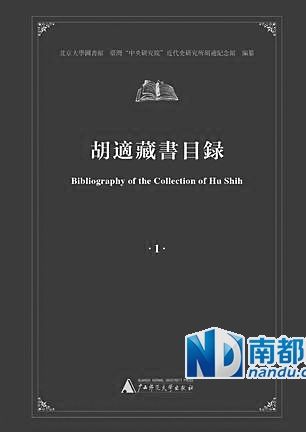
《胡适藏书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版,1680.00元。
作者:张书克
江勇振著胡适传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使得我们原本认为简单清晰的胡适的形象变得模糊起来。它告诉我们:此前不存在问题的,现在都有问题;此前没有疑问的,现在都有了疑问。它告诉我们:我们离真实的胡适还远着呐!
传说中的胡适
继第一部之后,江勇振所著胡适传第二部也出版了。按照江先生的计划,他的胡适传要写五部,每一部50万字左右。已经出版的两部,第一部65万字,第二部83万字,超出了江先生计划的字数。整个写作计划完成后,肯定是部巨著。
给胡适写传记的人可谓多矣。从胡不归、毛子水、吴相湘到白吉庵、胡明、沈卫威、易竹贤、章清,再到欧阳哲生、罗志田、邵建,如果说胡适是一场戏的话,唱过胡适这出戏的人已经够多了。
江勇振对于此前的胡适传记都不满意。对于江勇振来说,这些传记都大同小异。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传记作者被胡适牵着鼻子走,对胡适留下的日记、书信、自传等资料缺乏怀疑的眼光,不加鉴别地全盘接受,结果上了胡适的当,掉进了胡适设下的资料陷阱。
因为缺乏鉴别和怀疑,我们流传着太多关于胡适的传说:现代圣人、道德楷模、实验主义者、杜威信徒、自由主义者、及时雨、汉奸、战犯、肤浅、惧内,等等。在江勇振看来,许多问题,本来应该只是研究的起点,结果却成了结论。大家不思不想,不求甚解,不去怀疑和求证,把待证的假设作为结论,把学术研究的起点当成终点。
其实,不仅胡适本人的说法我们不去怀疑、不去求证。我们有太多关于胡适的传说。江勇振举了一个例子。根据林语堂本人的说法,胡适曾经资助林语堂2000银元(相当于现在的8万元人民币),使林语堂渡过了留学生涯中的难关。不过,吴元康根据档案资料考证,事实并非如此。即便有吴元康的考证,这个胡适资助林语堂的传说还在流传着。(参见江著胡适传第二部下篇第5-9页)
多年以来,经过胡适本人以及大家的努力,关于胡适的传说日积月累,已经堆积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胡适也几乎成了一个层层累积的传奇故事。在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前言》部分,江勇振都引了胡适研究《诗经》时的感慨:“两千年的‘传说'(tradition)的斤两,何止二千斤重!不是大力汉,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江著胡适传第一部前言第8页,第二部前言第8页)江勇振显然有意要做一个大力汉,推翻胡适研究中的种种传说。
在怀疑的基础上,江勇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江先生的确找出了很多新材料。许多资料,此前的研究者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当然也不可能想到要加以利用,比如杜威、葛内特保存的胡适书信,康乃尔大学的学生报、课程说明,《北京大学日刊》中的胡适动态等。能够挖掘出这么多新史料,已经是江先生绝大的贡献了。更重要的是,江勇振还下了一番笨功夫、苦功夫。对于那些胡适读过的书,尤其是对胡适有重要影响的著作,江先生都找来认真细致地阅读,并和胡适的著作进行比对,对胡适的思想追根溯源,找出其源头来。
我们来看看,在推倒胡适传说后,江勇振建构出的胡适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学术不端的胡适
胡适生活的那个时代,学术规范还没有建立,不甚讲究注释规范。江勇振认为,胡适一辈子都有引而不注的坏习惯。胡适援引别人的书、文章和观点却不加注脚,而且有拼凑抄袭的嫌疑。即使有时候有注释,注释也不规范,甚至有不老实的地方。(参见江著胡适传第二部上篇第116页的分析)用现在的标准来看,胡适可谓是学术不端的典型了。
江勇振发现,对于胡适经常谈的实验主义,胡适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刚开始,因为功夫还不到家,他并没有把握实验主义的精义,未能窥其堂奥,对实验主义存在很多误解和曲解。他经常挪用、误用乃至滥用杜威的思想和概念。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误用和滥用的典型,和杜威的思想相差甚远。所以杜威没有让他通过,使他晚了十年才拿到博士学位。江勇振甚至认为,胡适其实是一个披着实验主义外衣的实证主义者。他的基本思想倾向和史学方法都是实证主义的。
胡适不仅在创作中有学术不端的情况,在翻译时也有可指摘的地方。对于胡适翻译的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江勇振认真对照原文,指出了胡适的误译、漏译乃至胡乱翻译之处。江先生的工作使我们认识到,胡适的翻译是存在问题的,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江勇振还指出,胡适思想有杂糅挪用的特点。胡适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方便,把别人的观点拿来就用,也不注明是从哪里来的;而且,他善于把不同人物和派别的观点糅合在一起,而不去注意它们的区别和矛盾。
在我看来,胡适杂糅挪用的特点反映的也许是时代的特征。胡适那个时代,输入新学理是时代性的要求。学术上是否不端、注释是否规范,根本就不是胡适考虑的问题。而且,对于胡适这样才气很大的人来说,大概不屑于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地引述别人的观点和话语,总是要加以修改、变化和创造性的发挥。很多时候,他从别人那里吸取了灵感,然后加上自己的东西予以化用。
胡适杂糅挪用、引而不注的坏习惯给我们后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好在《胡适藏书目录》现在已经出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书目,结合胡适日记、书信和著作中的读书记录,按图索骥,顺藤摸瓜,认真读读胡适读过的书,总能找出一些胡适思想的渊源。
好名、好斗的胡适
胡适好名。这个连胡适自己都承认。早年在澄衷学堂读书时,其二兄胡绍之就写信责备胡适好名。(参见《胡适日记全集》第一册,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1页)
江勇振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细致分析了好名的胡适如何通过一番运作,来给自己脸上贴金。
1922年,上海《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ly Review )由读者票选“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在票选活动的过程中,胡适在自己编辑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抗议评选标准的偏颇,批评那是在华外国人的把戏,不能代表多数中国人的立场。胡适并且拟出了自己心目中的“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在江勇振看来,胡适的批评并不符合事实;而且,胡适的这一做法是有用意的、有目的的,近似于一种运作,起到了暗示、催票的作用。结果,胡适顺利入选“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名列第十二名)。入选后,胡适也忘了他此前对该评选活动的批评,有机会就向别人宣传自己是“当今中国十二大人物”之一。
江勇振还指出胡适好斗的一面。在江勇振看来,为了争夺话语霸权、文化霸权,胡适和各路人马展开了竞争和角逐。所谓文言与白话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以及《新青年》内部的纷争,都是在争夺文化霸权。最典型的是梁启超、胡适之争。他们两人关于墨子的争执,表面上是学术争鸣,其实可以看做是两代狮王的争霸战。看来赫胥黎不仅教给胡适怀疑,还教给他好斗。更有意思的是,胡适不仅做球员,还自兼裁判,宣布自己一方在各场论争中获胜。江勇振的分析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法西斯蒂的胡适
一些论者认为,1926年,胡适赞扬苏俄的大理想、大实验,赞成公有制,背离了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有左倾的表现。江勇振则恰恰相反,他认为,1926年的胡适赞成民族革命、颂扬极权政党,是胡适一生中最右倾、最法西斯蒂的时期。
1926年,胡适在英国做过多场演讲。他赞成当时正在国内进行的国民革命,并多方为革命辩护。根据这些演讲,江勇振认为,胡适由反对革命走向了“革命有理”,并且颂扬国民党在校园里吸收和组织学生的做法,礼赞党军一体化、高度纪律化的组织模式,明显是一种法西斯蒂的倾向(参见江著胡适传第二部下篇第309页、第378-381页)。江勇振还认为,和法西斯化的倾向相适应,胡适从他个人主义、世界主义的立场退步了,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倾向。
胡适“一度倡导法西斯主义”(该书封底宣传用语)?这倒是一个惊人的发现。不过,江先生的论证并没有说服我。我们不妨来看看沈刚伯的说法。
沈刚伯说,1926年他在英国见到胡适,两人有过一番谈话。沈刚伯问胡适,他在英国赞成国民革命、拥护国民党的演讲是否有意宣传?胡适回答说,他本来是反对武力革命和一党专政的,但是革命既然已经爆发,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胡适还说,当时中国所急需的是一个近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具有现代知识,只要它真能实行三民主义,便可有利于国,一般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支持。沈刚伯对胡适这番话的印象是:胡适是在“牺牲个人主张以顾全大体”。(沈刚伯:《我所认识到的胡适之先生》,原载《时与潮》第111期,此处据冯爱群编辑:《胡适之先生纪念集》,学生书局1973年影印再版,第9页)我想沈刚伯的这段记载还是比较可靠的。对于国民革命和革命党,胡适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但他认为革命既然已经开始,就只能接受这种现实,只是希望这段革命的痛苦能够早点结束。这是一种非常现实的态度,和他的基本思想倾向无关。而且,一般来说,胡适在国外的时候,从来不批评自己的祖国和政府,而是竭力维护国家和政府的形象,竭力为宗国辩护。在国内的时候,他才直言不讳地批评自己的国家和政府。
如此看来,江勇振把胡适在英国的演讲太当真了。他由此得出胡适右倾、法西斯蒂的结论,是没有说服力的。他没有区分,哪些是胡适的一贯主张,哪些是权宜之计、现实的考量;也没有区别胡适在国外和国内说话的不同分寸,难免上了胡适的当。
对肛门偏执的胡适
江勇振注意到,对于自己的病,胡适在日记中描述得最仔细、最锲而不舍的,不是心脏病,也不是脚气病,而是他的痔疾。因而,江先生认为,胡适对痔疾或者说肛门有一种偏执狂。
胡适的痔疾很多人都知道,可谓是广为人知。1930年,郁达夫为痔疾所苦时,还写信给胡适,问治病医生的地址。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知道胡适的隐疾,得益于胡适本人的大肆张扬。
1923年12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胡适的一封公开信。这是一封请假信,信中胡适提及了自己的痔疾。1925年11月10日,胡适致信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请求辞职,并请蒋把这封信刊载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信中详细叙述了自己的“肛门之病”以及治疗方案。胡适的做法使得北京大学的师生人尽皆知他有痔疾。
在给女朋友韦莲司的信中,胡适也不止一次提到了自己的痔疾。因此,胡适的痔疾不仅成了中华民国最有名的痔疾,并且还引起了国际友人的关注。
江勇振认为,胡适这样一个最最谨守隐私的人,把自己的恋情隐藏得那么深,却如此毫不遮掩地暴露自己的隐疾,一方面说明,当时的时代对躯体的暴露不甚禁忌;另一方面,也说明胡适有一种肛门偏执。而这种肛门偏执跟胡适的写作焦虑有关。江先生还认为,胡适巨细无遗地收集、孜孜不倦地保存自传档案,保留别人给他的信件,是肛门性格的典型特征。
江先生的说法很有意思,不过,需要医学专家进行更为细密可信的分析。而在我看来,胡适经常提及他的痔疾的原因也许很简单:因为他是作家,要经常坐着,所以受痔疾的困扰最大。当然,我的这个解释太简单、太肤浅了,弗洛依德听了会笑话我的:太没文化了。
一个真实全面的胡适?
江勇振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全面的胡适吗?我想这并不是江先生的用意所在。
江勇振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一个真实全面的胡适。
首先,江勇振的胡适形象并不全面。江先生似乎想要做个大力汉,推倒以前的一切传说,建立新的学术典范。这样当然就要舍弃此前学术界的很多共识,主要从事解构工作。所以,江著胡适传中考辨、考证的内容很多,直接描述胡适形象的内容相对较少,当然无法塑造全面的胡适形象。江先生这种写法在传记作品中未免另类,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阅读障碍。
其次,江勇振笔下的胡适当然不是真实的胡适,他只是江勇振的胡适,是江勇振主观理解和构造出来的胡适。在我看来,很多地方江先生都解构太过,其提出的很多新说都未必能够成立。
我想,江著胡适传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使得我们原本认为简单清晰的胡适的形象变得模糊起来。它告诉我们:此前不存在问题的,现在都有问题;此前没有疑问的,现在都有了疑问。它告诉我们:我们离真实的胡适还远着呐!要想接近真实的胡适,我们还需要一番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