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政商”并不是个体性的官商勾结这么简单,“而是通过一些机制,官与商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利益结构,或可称之为政商利益共构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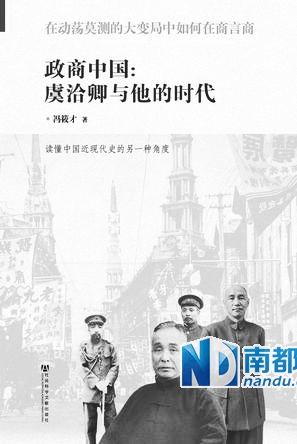 《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冯筱才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9月版,38 .00元。
《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冯筱才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9月版,38 .00元。王绍贝 媒体人,深圳
《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一书,以政商代表人物虞洽卿个人经历为经,以政商问题为纬,从这个跨越几代政府的著名商人经历入手,对晚清到民国时期的政商问题做了通观性的研究。此书对于我们认识民国历史具有参考价值,对于研究政商这一群体也有重要的意义,从政商的个案分析,总结这一时期政商结构演变的脉络,得出一些普遍性结论,无疑是此书的特色和价值所在。
“政商”又被称为“官商”、“官僚资本家”、“御用商人”等,但此书作者认为这些概念都不如“政商”一词来得准确,所谓“政商”并不是个体性的官商勾结这么简单,“而是通过一些机制,官与商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利益结构,或可称之为政商利益共构网络。”
日本最早使用“政商”一词来指称明治维新前后的“御用商人”,这些受明治政府扶持和发展的商人形成了日本最早的财阀(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为代表的四大财阀),政府通过扶持这些有背景的企业,从而“集中力量办大事”,对日本的现代化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而财阀既然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商业经营的特权,自然也要为政治家、政客提供资金回馈,日本近代的财阀政治由此形成,并仍然对日本政治的现状发挥着深刻的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处于“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最低地位,尽管古代商人靠商业发家致富,但他们的子孙却不会选择继续经商,而是向往转变为大地主或官僚。然而,这种商人的低贱地位到了近代社会忽然发生了逆转,在中国现代化的转型中,建设工商社会无疑是重要的任务和目标。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政商代表人物是胡雪岩,他通过与官僚左宗棠的关系,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成为政府粮饷、军火的供应商,从而获取暴利。进入“洋务运动”时代,晚清大力开展现代化建设,政商群体于是在中国兴起。
与胡雪岩不同的是,虞洽卿从做洋行买办起家。晚清中国的“买办”实际上是“中外交通的桥梁”,不仅是经济贸易上的交流,在地方政治与社会事项上,当时上海的买办也在发挥这种纽带作用。虞洽卿经常扮演一种调解人的角色,协助政府与洋人(外国商人、企业)、政府与民间商人办理交涉,从而为他个人积累了政治、商业的各种社会关系资源,也就是今天说的“人脉”。
虞洽卿早期的事业涉及金融、轮运、房地产、矿产等众多行业,从一开始就是有投机色彩的商人。就虞洽卿投资地产的方法来看,他很早就懂今日所谓的“借壳生蛋”之法。“如他曾借用创办公共设施的名义,援引官方力量介入征地,在兴建公共设施之后,可利用附属土地开发房地产或抵押图利”……“以公益之名圈地,事成之后,再划分部分土地以渔利,或变更用途以造房牟利,此种今天很流行的官商勾结开发房地产的策略,虞洽卿当时就运用自如。”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民族危机加重,虞洽卿则善于利用民族主义包装自己、扩展自己的商业利益。虞洽卿用抵制日本人在上海开办取引所的名义,游说政府建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并成为该交易所的实际控制者。但不可思议的是,打民族主义牌创立的上海交易所从一开始就与日本股本有关。“根据协进社与日本企业商定的办法,日资占十分之七。可见,所谓抵制日人一说,纯属对外宣传烟幕,无日人之支持,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也许就无成立可能。”
虞洽卿过去被我们看作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江浙财阀”代理人,视之为蒋介石扶持的御用政商,但这种简单化的意识形态划分其实不符合历史真相。作为一个商人,虞洽卿并没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政治依附对象。1924年,虞洽卿开始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为了扩展双方的势力,中共选择与虞洽卿合作,可见为了谋求个人权势的扩张,商人也会介入动荡的时局,尝试与各种势力合作,这种合作对象包括了时人眼中的“赤化派”。
然而,虞洽卿与中共的合作注定是短暂的,北伐没有完全胜利,蒋介石就发动了“清党运动”,虞洽卿通过面谈与蒋介石达成了一致的立场,完成了政治站队,此后便成为蒋介石控制上海这座中国最大城市的重要协助者。王晓籁回忆说:“北伐军到上海,蒋要钱就找虞,虞想办法就是国库券”,虞洽卿通过向社会、商界发行国库券为国民革命军筹集军费,帮助蒋介石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总体来说,虞洽卿的这种“政治投机”往往是形势已经比较明朗,基于商业利益的政治选择,这种情况用一句闽南话说就是“西瓜靠大边”,意即从自身利益出发,倒向势力强大或局势较有利的一方。商人如此,政客也是如此,对比较信奉实用主义的人来说,只要他的权势依然存在,虞洽卿仍然具备统战的价值。1936年,毛泽东就曾询问过冯雪峰,是否有可能与虞洽卿合作。
虞洽卿为政客倾尽全力当然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1928年,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经营陷入困境,由于扩张过快,虞氏资金链即将断裂,其开出的支票,上海已无银行愿意受理,似已认定虞陷入破产边缘。但是虞洽卿动用其手中各种人脉,甚至通过蒋介石的直接饬令,发行行业公债350万元,缓解了债务危机。1936年年底,虞洽卿私产在四明银行押欠款项总数达到460余万元。官营的四明银行饬令处理三北公司债务,但最终因蒋介石的缓颊而未能实行。到了1937年7月,抗日战争突起拯救了虞洽卿,战时环境下,“三北假外商名义航行,大获其利,同时币值贬低,数年债务,很快都偿清了”。
1928年,陈光甫在其日记中恨恨地说,虞洽卿以一个外行人办航运,债台高筑,经营混乱,而他到处开会,作演讲,像没事人一样,对此表示不解。但其实虞氏作为一个典型的“政商”其“高明”之处就在于此,他通过介入社会事务及政商关系经营积累社会资本。由于他有强大的官场人脉,以及社会动员能量,所以即使其借贷期满甚至拖欠一二十年,金融机构主事仍不能不顾“面子”而与他绝交。虞虽然经济信用极差,但是其社会信用能弥补前者不足,各方债主迫于情面或其他幕后交易,就不能公事公办,宣布其“破产”。他能周旋于两种资本的混合状态之中,如鱼得水,正是世人所谓的“长袖善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