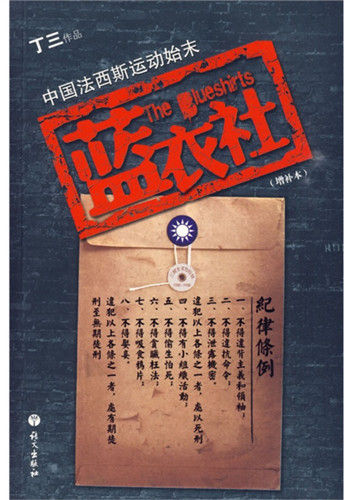 《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丁三著/语文出版社2010年版
《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丁三著/语文出版社2010年版(文/danyboy)
2010年,张大春写于上世纪的小说《城邦暴力团》在大陆出版。同年,一位名叫丁三的作者写于2003年的通俗历史读物《蓝衣社碎片》以《蓝衣社: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的名字增补再版。作家徐皓峰于2007年、2010年分别出版小说《道士下山》《大日坛城》,并成为2013年上映的电影《一代宗师》的编剧。2014年秋,刘和平编剧的连续剧《北平无战事》在大陆一时风靡。
以上提到的小说、剧本、电影和历史读物,在内容上都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共同点,那就是都有对民国期间活动于国民党体制内部某个秘密组织成员的刻画。张大春和徐皓峰笔下,描写的是民国时期一些身穿中山装、行踪诡秘、武艺高强的特工;《北平无战事》的镜头里,是民国时期几位作风清廉、忠于党国、手段残忍的年轻官员;丁三的作品则明确了这些人的隶属:蓝衣社。于是,这段关于蓝衣社的历史就随着文学影视作品的传播,越出了中国现代史、国民党党史等的疆界,以一种若隐若现、亦正亦邪的神秘形象逐渐为当代大陆的普通人所知。
一、
蓝衣社并不是一个严谨的称呼。
1931年,日本侵华野心毕露,中国的局势却并不乐观:民众一盘散沙、不少地方政权各自为政、南京政府成立后迅速官僚化和腐败化、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内斗不止。于是,一群志于救国救党的黄埔青年毕业生,由滕杰与其未婚妻陈启坤倡议,以贺衷寒、胡宗南、桂永清、邓文仪、康泽等黄埔学生为核心,包括非黄埔系的戴笠等人,筹备并于次年成立了“三民主义革命同志力行社”。这是一个标榜模仿德意纳粹党,标榜个人作风清白廉洁、组织纪律极为残酷严密的法西斯组织。第一,他们以蒋介石为绝对的唯一领袖;第二,他们不仅自己组织严密,还要通过残酷、严密的方式将全国民众强行组织起来,铲除异己,形成能够“攘外安内”的力量。蒋介石对这个自发形成的青年组织十分看重,亲自担任力行社社长,并赋予了力行社一些非常重要的权力,社内的高级成员多是党内少壮派,如贺衷寒曾是与陈赓、蒋先云并列的“黄埔三杰”之一,邓文仪则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力行社成立后,这些高级成员拥有了更多亲近蒋介石的机会。1933年,贺衷寒以力行社为核心,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按照丁三的说法,同年,刘健群公开宣称中国有着一个类似德国冲锋队和意大利黑衫军的“蓝衣社”,于是蓝衣社的名字不胫而走,成为了这一组织最为人所知的名称。
1932年之后,力行社先后在军队、政府、企业、大中院校及各类社会团体中建立了极为广泛的外围组织。随着中日局势的日益紧张,蓝衣社的走向又有了两个特点,一个是大量军训青年,为抗战作人力上的准备;另一个则是戴笠负责的特务处实力上升,他们招募间谍,训练政治警察,对反蒋反政府的各类人士包括左翼、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公开投敌的汉奸与混入内部的日本间谍等进行打击、镇压与消灭。此消彼长,戴笠的组织逐渐脱离蓝衣社隶属,大有独立之势。不久西安事变突然爆发,蓝衣社的几位头目邓文仪、贺衷寒因为在蒋介石处失宠,就站在了“武力解决”事变的立场上,与何应钦一样想借刀杀人。不料蒋介石平安归来,蓝衣社彻底失去蒋的信任。1937年底,蓝衣社的主体被纳入新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特务处则由戴笠改组为“军统”。次年,蓝衣社解散。
二、
蓝衣社的历史与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 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基本重合。即使是大陆的历史教科书,也不得不承认这十年间,因为国际上经济危机爆发导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喘息时机”,使得国内经济发展迅速。政治局势也趋于稳定,“中原大战”结束了,苏维埃政权在不断的围剿之下被迫北上长征,实力迅速下降,若非偶然发现了刘志丹的陕北红军,几乎就要败退到苏联了。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积极发起了党内政界的反腐败运动和在民间的禁烟运动、在农村发放小额信贷的“农村复兴运动”、致力于提高国民素质的“新生活运动”及金融领域的法币改革等。这些活动是国民政府在“统一”国土之后戮力建设的重要行为,并在经济复苏的条件下成效显著,也争取了国内一定的民心,而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除了法币改革多依仗孔宋家族外,几乎背后都有蓝衣社的影子:有些以力行社的名义直接办理,有些由力行社、复兴社社员总揽其事,有些通过各种外围组织广泛发动。可以说,没有蓝衣社强大的组织能力和脚踏实地的工作,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势必会打折扣。
当然,相应的,这一时期对左翼运动来说则是白色恐怖的低潮。国内政治经济相对稳定,民众的革命意愿就会相对降低。国民政府为了铲除异己、控制民众,通过蓝衣社采取了诸如保甲制度、书报审查制度等手段,残酷压制反政府的声音与行为。也是在这一时期,蓝衣社推动了大量“群众运动”,比如民间公共区域要悬挂蒋介石头像、老百姓见到头像要肃立敬礼等。群众们被组织起来了,有文化的青年被吸纳到蓝衣社的外围组织中,乡村的青年人被编入了壮丁队、反共义勇队。妇女们被编入妇女队,少年儿童们被编入童子军、少年义勇队,老年人被编入长老会。甚至到了中后期,蓝衣社大量收编民间的会道门组织,将其改编为忠义救国军——张大春《城邦暴力团》和徐皓峰笔下的一些武艺高强的特务形象,并不是凭空捏造,民国的许多所谓武林门派的人士,就是通过忠义救国军这一渠道被纳入蓝衣社的外围的。
三、
纵观蓝衣社的历史及其功过,会发现这个组织尽管受法西斯主义的引导,但却有着自身特点。最主要有四点。一是组织性,蓝衣社具有严密的组织,从核心的力行社到外围的众多群众组织,从极少数掌握权力的上层人员如“四大金刚”“十三太保”到几十万鱼龙混杂的基层社员,这几乎是再造了一个“青年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也是一个革命党,有革命的目标,要统一四分五裂的国土,要凝聚“一盘散沙”的国人,要驱逐外国势力。但是,实现目标需要人,特别是需要干部。众所周知,国民党的党组织很松散,几乎可以说是陈氏家族的“政治私产”,因此组织能力极为涣散。蒋介石要想把权力伸到军阀所在的地方,伸到国民党统治没有覆盖的地区,从而完成一系列治国治兵的举措,就需要较为严密有效的组织。所以,组织性、动员性是蓝衣社重中之重的特点。
二是青年性。国民党之所以从北伐时期的革命党迅速腐化为一个千疮百孔的官僚机构,其中一个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辛亥前后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年在30年代已经蜕变为四五十岁、有家有口、高居官位的中年大叔,革命热情日益消退。而这样一个腐败堕落的官僚体制是很难应付虎狼一般的日本的。所以,蓝衣社最初的目标,就是让尚未腐化、热血尚存的青年人来与国民党利益集团分庭抗礼,为抗日积攒力量。而对蒋介石来说,这些热血青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民党在组织方面的短板,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青年干部。多年之后,当我们这些青年人在《北平无战事》的荧屏上,在丁三的书里看到这些同龄人时,不由的会产生一种强烈莫名的共鸣,他们虽然走的路是专制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但他们引领民众、反对利益集团、改造官僚体制和抵抗日寇的一腔热血,仍然难以磨灭。
三是自律性。既然是要克服官僚主义,建立强有力组织的青年团体,那么成员的自律性是少不了的。滕杰在设计力行社的时候,中共的自律性曾给了他很大的触动和启发。力行社吸收早期核心成员,多数也具有清教徒和理学家一般的自律精神,他们相互监督,卖力工作,天天加班,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不纳妾。工作上坚决廉洁自守。这一特点,既有法西斯团体标榜铁血精神、蔑视世俗享乐的原教旨性,也与中国传统特别是宋明儒学的自律精神相关。这种自律的动力,既有对抗日救国和国民革命的信仰,也有对蒋介石个人的忠诚,也有为了出人头地的纯粹个人私利。——反讽的是,当代的青年人“自律”的动力,多数是上述的第三种,只是换了个词语,叫“成功”。
四是秘密性。既然不必担心像地下党那样不敢公开活动,一个“体制内”组织主动隐藏起来的目的就很值得玩味了。他们的行动如同看不见的武器,给很多人带来恐惧感。但最主要的目的是用秘密性来保证自身血液的纯粹,越可靠的同志,离核心组织就越近,只有真正的同志才能被吸收进来。然而,从力行社到蓝衣社,这一保持“队伍的纯洁性”的意图显然是失败了,因为蓝衣社从未进行过马列主义政党式的内部清洗,反而不断地扩大队伍,只进不出。而且,作为秘密组织的蓝衣社不断地干一些暗杀之类的脏活,让一些有正义感的人十分鄙夷。最终,这一“秘密性”不仅没有阻挡组织的堕落,反而使劣币成功驱逐了良币。
四、
那么,问题来了:蓝衣社为什么会出现?对蓝衣社的行为如何褒贬?我们今天了解这个在现代史上仅仅存在不到10年的青年组织,意义何在?
丁三在《蓝衣社》这本书中也试图回答这几个问题。他用饱含深情、充满同情的笔触描写了蓝衣社的这段历史。在他看来,蓝衣社的目的是改造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把民众组织起来、凝聚起来。而中国之所以“一盘散沙”,根源是长久形成的国家统治力量的专制剥夺了人民的自主意识,人民逐渐习得,在强大的国家统治力量面前,唯有“懒于”和“惧于”自我组织才是安全的。当蓝衣社用更为专制、暴力的手段强行组织民众时,无异于饮鸩止渴。因此,作者虽然对蓝衣社的一些成员和历史功绩持褒扬态度,但最终还是否定了蓝衣社这段历史。不过,作者在书的最后却说,蓝衣社组织民众的归于失败,根源是民众缺乏心甘情愿被组织的“信仰”,而且也不够广泛,相反,中共既有足够吸引人的理论,更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方面具有空前的力度、广度和深度。
这个看法是有趣的。中共作为“先锋队”居于核心位置,各类妇联、儿童团、共青团、工会等处于外围,这一严密的社会控制结构形成了强有力的组织力量,形成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从解放前直到现在,这一“走群众路线”的理论话语始终存在于党的建设理论体系里。
事实上,国共两党在中国的近现代化上具有相似的革命目标和历史任务,在组织方式上也有许多共性,甚至可以说主要在组织程度和自我净化能力上有所不同。于是,蓝衣社的历史蕴含的真正深刻的问题是:近现代中国,是否一定要经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过程?是否能够说,只有这种对国民高度组织化,才能突破传统中国形成的从思想、社会结构到利益集团对个人的压迫以及国际势力的干涉?
抗日战争与朝鲜战争的胜利、国土的基本统一、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似乎证明了上述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蓝衣社这一同样高度组织化的机构的失败,则提供了另外的一面镜子。蓝衣社的解散,与其说是一系列具体事件和高层成员的问题导致的,不如说是被当时的国民党体制所吞噬的,蓝衣社亡于自身逐渐的官僚化、腐败化和内部派系倾轧。革命的团体最终成为革命的对象,就像一条贪吃蛇,一旦咬到自己的尾巴,游戏也就终止了。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成就卓著的今天,改造“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的目标真的实现了吗?当全民的“团体生活”已经由组织强行包办,不能在基于自身意愿的基础上过个人自治或社团自治时,这会是一个充满活力、自由发展的共同体了吗?在这一高度组织化的体制内部,个人是组织的傀儡呢还是主人?为什么中国的国民不组织起来就是一盘散沙,组织起来就会产生等级和奴性呢?
蓝衣社的失败证明了,改造一盘散沙的国民,靠外在的组织只能成一时之功,真正强有力且充满活力的共同体,需要的是个人的自治、社会组织的自治。当然,这已经是另外的问题了。


